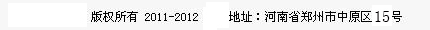从宏观上看,电子分歧是在用未来的能量转移现在的电子,而从微观上看,电子分歧又是在用可能的反应推动不可能的反应。比如说,细菌和古菌要让氢分子自发地把电子交给铁氧还蛋白,就是一个不可能的反应。
因为氢分子一旦交出电子就会变成氢离子,而氢离子比铁氧还蛋白的氧化性更强,也就是结合电子的能量更强,所以那对电子即便交出去也是放鸽子,立刻就会返回来,与氢离子重新结合成氢分子。
这种“不可能”与氢气直接还原“二氧化碳”的不可能是同一种“不可能”。当然,这种不可能是指自发的不可能,如果能给那对电子强塞一笔额外的能量,这个反应当然还是会发生的。比如矿物管壁上的铁硫矿晶体,或者能量转换氢化酶,都是利用天然氢离子梯度中蕴含的能量办成了这件事。
可是,生命既然要离开天然的氢离子梯度,又要去哪里找来这笔能量呢?——就从可能发生的反应里出吧!再让我们说得具体些。细菌和古菌用来催化电子分歧的酶大多需要核黄素,也就是磷酸化的维生素B2,所以统称“核黄素依赖型电子分歧酶”。
这个电路的最右端是氢分子,是整个反应的“供体”。供体结合在一个铁镍簇上,通过一条铁硫簇主线抵达了一个核黄素,那是电路的“门控”。门控又发出了两条岔路:下方的岔路通往等待还原的铁氧还蛋白,那是整个反应的“目标”;而上方的岔路就通往某种氧化性辅酶,我们可以沿用正文的比喻,叫它“抵押”。
在电子分歧酶的具体催化过程中,开头的部分没什么好奇怪的,和我们之前的许多例子都是一个原理:右边那一串铁硫簇的间距都在1.4纳米以下,这足以引发一种诡异的量子跃迁效应,电子可以像跨过哆啦A梦的任意门那样,从一个铁硫簇上消失,同一个瞬间又在相邻的铁硫簇上出现,而氢分子的那对电子,就能以这种方式转移到核黄素上。
所以铁氧还蛋白原来需要拿走氢分子的电子,现在就变成了要拿走核黄素的电子。但这仍是同一种不可能,毕竟铁氧还蛋白连氢分子的电子都抢不走,又何德何能抢走核黄素的电子呢?这就多亏了核黄素作为“门控”的独特性质了。一般的物质如果失去了一个电子,就更难失去第二个电子,这就好像挖坑总是越深越难挖。
反过来也一样,如果得到了一个电子,就更难得到第二个电子,这就好像堆土总是越高越难堆。但核黄素不太一般,它能接受两个电子,而且接受第二个电子比接受第一个电子还容易,也就是说,它只要拿到了一个电子,立刻就会疯狂地再去抢夺另一个电子,这使它拥有了挺强的氧化性。
反过来也一样,得到了两个电子的核黄素要失去第一个电子需要不少的能量,但要继续失去第二个电子就只需追加一丁点的能量,恨不得立刻把另一个电子送走。既然如此,那个“抵押”就能派上用场了:它们具有不错的氧化性,有本事抢来第一个电子,这将是一个自发的反应,一个释放能量的反应,而这份能量就足以使核黄素的第二个电子变得非常烫手,核黄素会按捺不住地想要把它送走。
奈何那个抵押一次只能接受一个电子,于是,核黄素就会一反常态地大发善心,顺着下方的通路,硬把第二个电子塞给了铁氧还蛋白。而抵押一共能够接受两个电子,所以这整个过程会发生两次,每次都把第一个电子交给抵押,再把第二个电子交给铁氧还蛋白。通过电子分歧,氢分子交出了两个电子,变成了氢离子。
这对电子又走上了两条不同的岔路,一个参与了热力学上可能的反应,释放了许多能量;另一个则直接利用了这份能量,投入了原本不可能的反应,制造了原本不该出现的产物,即充满了电子的铁氧还蛋白。当然,那个抵押也被消耗掉了,所以在之后的代谢里,细菌和古菌都要挪用细胞代谢的能量,把它们循环回来。
至于这个抵押具体是什么,在产乙酸细菌那里,辅酶NAD和H;但在产甲烷古菌那里,正文却只是概括地说了个“二硫键”。但实际上,那是由两种辅酶,辅酶B和辅酶M,以二硫键联合起来的“异二硫辅酶”——所以古菌的电子分歧酶会更具体地叫作“异二硫还原酶”。
我们说过,在蓝细菌出现以前,地球上几乎没有游离的氧元素,地热活动释放的硫元素已经是最接近的替代物了,所以那时候的过硫化物恐怕就好比今天的过氧化物,已经是非常强的氧化剂了。在电子分歧的过程中,异二硫辅酶作为“抵押”夺取核黄素的第一个电子可以释放出单位的能量,而把核黄素的第二个电子塞给铁氧还蛋白只需86单位的能量,的确是绰绰有余。
但是反过来,异二硫还原酶经过抵押就重新变成了辅酶M和辅酶B,它们要怎么重新结合成异二硫辅酶呢?这件事要分两步走。首先,在乙酰辅酶A路径的长分支末端,二氧化碳已经被还原成了甲基,携带在辅酶四氢蝶呤上,这个甲基本来应该继续与一氧化碳结合成乙酰,但是为了赎回抵押物,一种甲基转移酶就会把一部分辅酶四氢蝶呤拦截下来,把它的甲基转移给辅酶M,成为甲基辅酶M——而这个过程就会释放很多能量,如正文所说,甲基转移酶可以借此把氢离子泵出细胞膜去。
接着,这个甲基辅酶M仍然带着一些额外的能量,它再与辅酶B相遇,就异二硫辅酶以甲基为代价,完成了循环。能恢复成异二硫辅酶,同时释放出一份垃圾甲烷了。异二硫辅酶以甲基为代价,完成了循环。
如果不是对死亡充满畏惧,人类就不会对生命充满期冀。在过去的几天中,作者一直想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哲人或者诗人,他想要写出形式上戛然而止,内容上隽永悠远的句子,好结束他出版的第一本书,但是他似乎做不到。倒是这种殚精竭虑让他每天睡醒前都会做一些光怪陆离的梦,似乎有五光十色的核酸分子在眼前飞舞,又或者是千奇百怪的拼图整理不完。
但也可能是他记错了,梦里是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到处都是前所未见的秘境,只是每当他想要踏入其中一个秘境一探究竟的时候,他的“梦境制造者”就不得不承认自己只是一个平凡的人类的大脑,即便是做梦也只能营造出“神秘”的感觉,却不能真的杜撰出任何一种感官不曾体验过的事物。
于是,编不下去的梦境轰然崩塌,南风与鸟鸣,天光与人声,一切感官体验就像银河冲垮了穹窿,倾泻而下,一刹那灌满了作者的胸腔。他醒来,看见窗外是仲夏季节湛蓝的天空,上面粘着丝丝缕缕的层云或者卷云,当云被罡风吹散,那些光怪陆离的梦也就被忘却了——大脑刚刚结束睡眠的时候,边缘系统的海马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工作,那些发生在新皮层里的梦境无法转化成记忆,于是就像内存里没有保存的临时数据,永远地消失了。
的确,我们的一切心智都是大脑中的神经活动,那是已知最复杂的信息处理活动,但大脑所能处理的一切信息归根结底都源自感官的输入,所以人类永远都不能想象自己没有见过的东西,哪怕是做梦也不可以。
所以既有人把感官看作心智与现实的唯一接口,认为任何知识只有追溯到“感官体验”才有可信度可言,才值得拿来讨论,也有人把感官看作禁锢精神的囚牢,相信感官带给我们的只是香遇浮华,唯有冲破了感官的束缚,获得了某种形式的“心灵体验”,才能触及至高无上的智慧真理。
如果把人类视为一种刚刚降世的动物,我们会遗憾地发现他们的感官粗糙而迟钝,远远不能满足那发达心智的旺盛需求。所以毫不奇怪,一切古老的信仰都会把后一种看法视为正当,区别仅在于要如何获得那种沟通神圣的“心灵体验”。
通过致幻药物的神经干扰,通过集体狂欢时的意识游离,通过天马行空的通感联觉,通过打坐入定后的深度冥想,通过自圆其说的天人交感,通过世传典籍的微言大义,通过虔诚投入的祝祷弥撒,通过神职祭司的中介传达……总之是一种神秘而不可直见的东西。
这样的殚精竭虑耗尽了古往今来不知多少人的毕生心血,然而当我们静下心来打量这些心灵体验的成果,不先入为主地把任何一个当作正道或者异端,那些被古老信仰视为终极奥义的东西就都与一场光怪陆离的大梦毫无区别了。神祇与恶魔总的来说是个长老、英雄或者君王,但是那些最叫人印象深刻的动物也都可能被先民撷取一些标志性的结构,比如翅膀、犄角、蹄子、尾巴、爪牙,甚至整个脑袋和躯干,一起拼凑在神魔身上。
神魔所做的一切,也无非是喜、怒、哀、乐、怜悯、作弄、好奇、猜疑、欢爱、征伐,顺带创造了宇宙、生命、人类乃至先民最在乎的一切东西,并且出于同样的原因操纵着人们心心念念的事务——起先是气象和生殖、狩猎和耕种、战争和疾病,然后就有商业和工匠、智慧和艺术、财富和繁荣,终于发展成了抽象概念上的苦难与罪恶、福音与极乐。